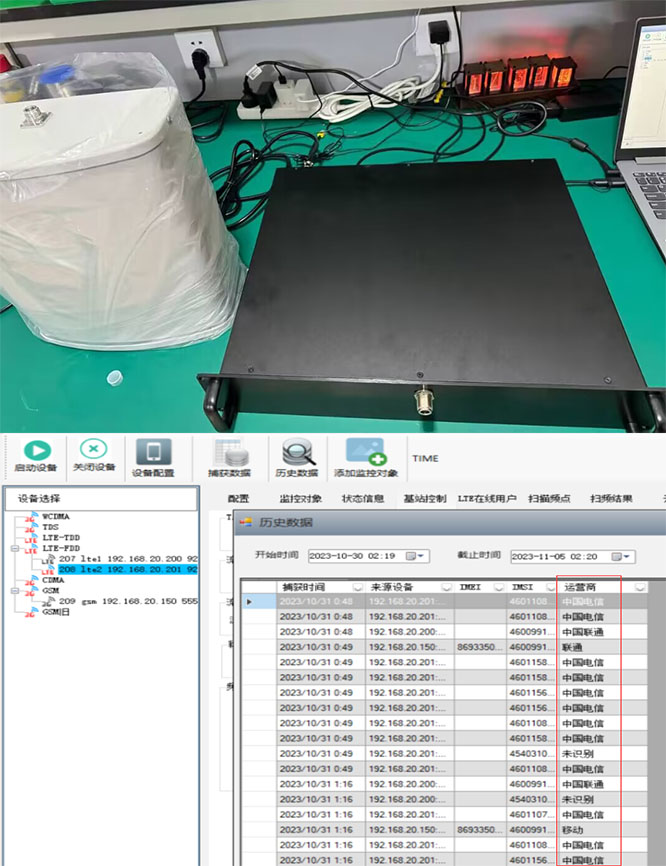陈为村抱着烈士陈淑彬兄弟俩的画像,在太爷爷太奶奶坟前百感交集。

陈家一直保留着的老屋。

陈淑彬烈士(左)与陈淑标烈士的画像。

陈淑彬烈士的印章。莒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提供

医务人员采集陈淑彬烈士侄子的DNA。莒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提供

莒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到陈淑彬烈士的亲属家中走访。

莒县烈士陵园。莒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提供
“太爷爷,太奶奶,我把二爷爷带回来了,现在就和您二老团聚……”9月14日,山东省莒县陈家河水村,刚受邀参加完第十二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的陈淑彬烈士大哥的长孙陈为村,一边将从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带回的一捧土撒在太爷爷太奶奶的坟丘上,一边轻声诉说……
物证闭环确认“此陈淑彬就是彼陈淑彬”
2022年9月16日,辽宁沈阳。祖国以隆重的仪式迎回第九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在这批88位烈士遗骸及相关遗物中,全国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发现一枚印章。尽管岁月侵蚀,但“陈淑彬”3个字依然清晰可辨。经查阅抗美援朝纪念馆相关资料,山东省莒县陵阳镇陈家河水村的烈士陈淑彬进入工作人员视野,他们当即通过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联系上莒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接完电话,莒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科科长付一凡就翻阅起《莒县烈士英名录》,发现陵阳街道(原陵阳镇)陈家河水村确实有一位叫陈淑彬的烈士,但名录上记载的陈淑彬是志愿军第73师38团战士,牺牲于1951年10月,这与全国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要找的印章主人、牺牲于1953年7月的第73师218团的陈淑彬信息不符。
“难道此陈淑彬非彼陈淑彬?”为尽快确认烈士身份,他们决定启动DNA比对程序。由于陈淑彬烈士直系亲属均已离世,莒县的工作人员只好从烈士的8位侄子中采集DNA,并送往全国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做比对。
烈士遗骸DNA提取难度较大,与亲属DNA比对的周期也很漫长。在等待结果的日子里,莒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深入村中调查走访。陈家人告诉他们,他们家不仅有陈淑彬烈士,还有陈淑标烈士,他们是亲兄弟,都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的,并拿出两人的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捧着破损严重、字迹比较模糊的证明书,细心的付一凡发现,其中单位信息竖着写的“二”和“一”,乍一看就是“三”,当时的登记人员也不了解部队,便将“二一八团”登记为“三八团”;经反复核对,牺牲时间也是当时的登记人员笔误造成。单位对上了,但此陈淑彬究竟是不是彼陈淑彬?谜团解开唯有等DNA比对结果。
等待是漫长的,等待更是揪心的。“自从采集DNA后,每次去给爷爷奶奶上坟,我都要和他们念叨念叨二叔的最新消息,因为我知道二老在九泉之下盼着二叔回家。”陈淑彬烈士的侄子陈常练红着眼圈说,等比对结果这3年,对陈家人来说日子漫长的就像过了一个世纪。
今年清明节前夕,全国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突破战争遗骸DNA提取、复杂亲缘关系鉴定等关键技术难题,在可靠的数据支撑下,确认了8位归国志愿军烈士遗骸身份,陈淑彬的名字赫然在列。印章、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和DNA数据形成的物证闭环,最终确定“此陈淑彬就是彼陈淑彬”。
消息传来,陈家人奔走相告,72年的思念与等待,在这一刻化作绵绵无尽的泪水。
村里人都说,这兄弟俩是当兵的好材料
随着陈淑彬烈士身份的确认,“兄弟保家国,一门两忠烈”的故事在当地越传越广。
20世纪20年代,陈家河水村的陈希庆、陈于氏夫妇先后生育4个儿子。孩子们一天天长大,脾气性格也逐渐显露。老大陈淑彩,为人老实;老二陈淑彬,身体灵活;老三陈淑标,机智聪明;老四陈淑朋,厚道本分。据村里老人回忆,每次谁家伐树,爬树拴绳子的任务总交给陈淑彬,他腾挪几下就能爬上树梢。陈淑标打小就聪明,无论是木工活还是瓦工活一看就会,他还会自制土枪打野兔。村里人都说,这兄弟俩是当兵的好材料。
1947年10月,华东野战军第7纵队在莒县征集一批新兵,24岁的陈淑彬和19岁的陈淑标争着要去。深明大义的陈希庆夫妻俩一合计,同意了兄弟俩的想法。
“咱穷人家的孩子,别的没有,有把子力气,到部队后可要舍得出力啊!”临行那天,天还没亮,陈于氏就早早起来,用全家人舍不得吃攒下的白面给哥儿俩包了一顿饺子,并叮嘱他们到部队好好干。
儿是娘的心头肉。陈于氏强忍泪水,颠着一双小脚,把两个儿子送到村西通往县城的公路上。瑟瑟秋风中,她挥动着手臂,直到看不见孩子们的身影……
兄弟俩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到部队后,先后参加胶东保卫战、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解放浙江等重要战役战斗,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1952年7月,兄弟俩所在的第73师218团接到配属23军的命令,9月中旬旋即入朝参战。
1953年,规模宏大的夏季反击战役打响。自7月6日开始,陈淑彬兄弟俩所在部队对盘踞在281.2高地的韩2师展开反击,接连4天共打退敌人47次反扑,歼敌1500余人。在这场反击战中,218团涌现出“向我开炮”的孤胆英雄于树昌等一批战斗英雄。不幸的是,担任副班长的陈淑标壮烈牺牲,而陈淑彬既没有找到遗体,也没有留下遗物,只能暂作失踪处理。直到1958年10月,才认定陈淑彬为烈士。
“第九批归国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相关遗物发掘地域,是志愿军第73师218团牺牲较为集中的韩国江原道铁原郡,也就是218团反击韩2师的281.2高地及附近地区。陈淑彬与弟弟陈淑标都是在这场反击战中牺牲的。”付一凡说,同一天入伍,同一场战斗牺牲,同样马革裹尸埋骨他乡,陈氏兄弟的事迹可歌可泣,也令人扼腕。
“老屋不要拆,拆了俩孩子回来就找不到家了”
秋日的沂蒙山,处处都是丰收的景象。漫步县级文明村陈家河水村中心街,成荫的绿树分列两旁,盛开的鲜花,整洁的村居,优美的环境,给人一种舒爽惬意的感觉。这时,一座破败的老屋突然闯入眼帘,让人倍感突兀与不解。村民们告诉记者,这座保留至今的陈家老屋,背后有一段与烈士相关令人泪目的故事。
1954年7月,陈希庆从莒县民政局领回三儿子陈淑标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和他的遗物:一顶军帽、一双鞋、一个搪瓷茶缸。白发人送黑发人,伤心的夫妻俩一宿未眠。第二天,他们含泪掩埋这些遗物,为陈淑标立了个衣冠冢。
对于音信皆无的二儿子陈淑彬,陈于氏心中一直有种不祥的预感,但她从没对人说过。1958年底,当县里将陈淑彬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送到陈希庆家时,失去两个儿子的陈于氏放声大哭,多年压抑在心中的思念、担心和痛苦瞬间爆发。由于没有收到陈淑彬的任何遗物,夫妻俩始终不相信二儿子已经牺牲,总盼着有一天会出现奇迹,连陈氏的族谱里也这样写着:“陈淑彬当兵 没信,陈淑标当兵 烈士。”
两个儿子的牺牲,对夫妻俩打击很大,特别是陈于氏。陈淑彬烈士四弟的长子陈常宗回忆说:“小时候,每次村里放露天电影,奶奶总要先问我演什么,如果内容是打仗的,奶奶就不看,说是看了伤心。有一次,偶然看了抗美援朝战争题材电影《奇袭》后,奶奶回家哭了整整一宿。”
“那些年,每到清明节,奶奶都会煮上两碗面条,站在村西头公路口,遥望二叔当年参军走的方向。有一年,清明节那天下起了大雨,已是80岁高龄的奶奶站在雨中,呼喊着二叔的乳名,任凭雨水泪水交织在一起……”提起奶奶对二叔的思念,陈淑彬大哥的长子陈常练,脑海中时常会出现这些让他永生难忘的画面。
陈常练告诉记者,奶奶家门楣上有两块“光荣人家”牌匾,老人视此为至高荣誉,擦的一尘不染。有一次,他用手拍了两下,被奶奶狠狠训斥了一顿。
1973年夏,一场大雨让陈希庆家的房子成了危房,他便在屋后又盖起3间新房。新房盖好后,院子中间的老屋就影响了视线与出行,每次进出都要绕着老屋走。孩子们和亲戚朋友都建议把老屋拆了,但陈希庆坚决不同意,也不说原因。“直到爷爷临终前,这个谜底才解开。那天,爷爷拉着奶奶的手说:‘老屋不要拆,拆了俩孩子回来就找不到家了。’说完就闭上了眼睛……”每每说起此事,陈淑彬大哥的次子陈常胜都要抹眼泪。
陈希庆带着遗憾离世后,陈于氏更加思念埋骨异国他乡的两个儿子。有一年,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执意要孙子陈常宗用小推车推着她,到30里路外的县城,找到民政局工作人员说:“能不能快点儿把俺儿的尸骨找到啊!”看着老人急切的神情,工作人员含着泪水劝她回家等着。这一等,又是好几年,直至老人去世,也没等来儿子埋骨何处的消息。临终时,她留下遗言:找到陈淑彬和陈淑标的遗骸,带他们“回家”,上坟的时候别忘告诉她一声。
山河锦绣,英雄归来。2022年9月16日,漂泊异国他乡70年的陈淑彬与他的87位战友遗骸回到祖国温暖的怀抱。
从回国到回家,从无名到有名,科技与等待让陈淑彬烈士终于“回家”,陈淑标烈士仍埋骨他乡。陈家河水村的村民们说,每天看到那曾经承载陈家兄弟成长记忆的老屋就会想起两名烈士,这里已成为他们缅怀烈士的最好去处。(黄永仓、卢军)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黄永仓摄
![[field:title/] [field:title/]](/uploads/allimg/c251001/1K92U39132V0-19158_lit.jpg)